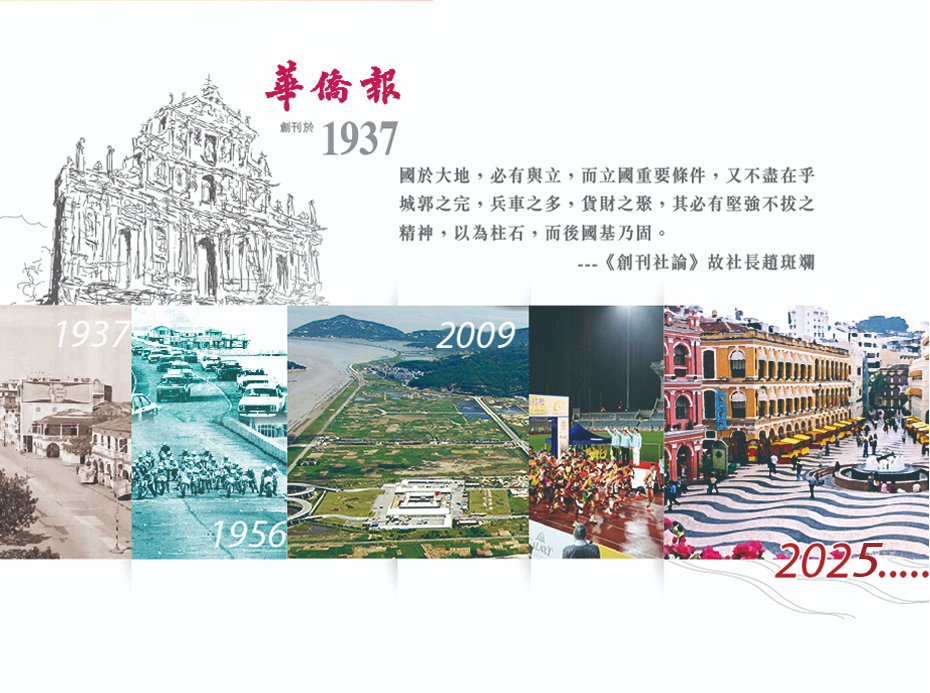「『嘎嘎』是高興;『喔喔』是難過;『咕恰』是生氣或害怕……」一身迷彩服的余建華邊模倣著猴子的動作,邊發出各種叫聲。
因「懂猴語」,今年67歲的他被認為是中國特有物種滇金絲猴猴群最親近的護林員。而二十多年前,他卻是十里八鄉有名的獵人。
余建華出生在白馬雪山南線一個有狩獵傳統的傈僳族村落——雲南省維西縣塔城鎮響古箐村民小組。作為一名孤兒,為了生存,他十多歲就擁有了豐富的叢林獵殺經驗。
「當時賣掉一隻熊掌,就能過上一周吃飽飯的日子。」他說,「猴子也是獵人們的目標。只是我沒獵過。」
滇金絲猴又稱黑白仰鼻猴,主要分佈在中國白馬雪山一帶。牠們有著與人類相似的神情、習性、社會分工和行為規範。
然而,由於當地獵人的獵殺和伐木對棲息地的破壞,這些猴子一度瀕臨滅絕。到20世紀80年代,當地人也很難發現滇金絲猴的蹤跡,即便是在外界最早發現猴子的白馬雪山北線的德欽縣。
中國於1983年針對滇金絲猴保護建立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而此時,保護區與一直靠山吃山的周邊群眾之間的矛盾幾乎一觸即發。
保護區周邊7.5萬貧困人群經濟收入的80%來源於木材和採集林間產品。白馬雪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護局維西分局局長鍾泰說,直到上世紀90年代,附近的村民家裡還能見到盜獵的岩羊頭骨和動物皮張。
「過去,為了偷砍樹木,全村19戶村民家家有運輸車輛。」德欽縣通堆水村小組老組長尼瑪說。
1999年,保護區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決定探索「社區共管」,保護的同時,著力解決周邊居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響古箐和通堆水等幾個村子都被納入試點。試點工作初始,有村民大聲質問尼瑪:「憑什麼不讓砍樹?」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沒人願意摧毀自己的家園。」鍾泰相信,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家園,而家園包括村莊,也包括周邊的植被、河流和森林,當然還有猴子。
鍾泰與同事們為村民修建自來水管,用新型材料替換房頭木板,手把手教村民種植玉米等作物,建立社區農作物種子基金,以及開展林下產品如松茸、羊肚菌和蟲草的研究。
這種有些另類的生態科研工作進村入戶,最終改變了社區居民傳統的資源利用方式。許多村民僅靠撿松茸、羊肚菌就有三四萬元的年收入。同時,一些村民被吸納為護林員,參與林區巡護。
「他們說服我做護林員,那時我還被叫作『小余』。」如今的「老余」,不經意間已呵護滇金絲猴二十多年。他已能通過細微的差別,分辨出生活在響古箐片區內68隻猴子的每一隻,並通過叫喊聲來了解牠們的快樂或憤怒。
現在,他依然每天帶上兩個饅頭和一壺水,和村民一起進山巡護,每周輪休一天。目前,響古箐村民小組總共46戶人家中,就有護林員40人。
臨近中午的響古箐山林裡,猴群以家庭為單位分散在樹葉遮蔽的枝丫上,許多家庭都帶著一兩隻幾個月大的小猴子。當大公猴吃飽了,摟著母猴一起坐著打瞌睡的時候,這些萌萌的小猴子依然不停地在樹枝上攀爬、跳躍或打鬧。
「看看牠們,是不是像極了小孩子,皮得很。」余建華說,猴群每天都會換一個過夜地;為防止生病和破壞環境,一般等牠們選定了地方,他才下山。「有時,猴子扯著我的褲腳不讓我走。」
近年來,社區共管模式已經在白馬雪山周邊廣泛推廣。保護區內的滇金絲猴數量翻了一番,另外14種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數量也穩步增長,包括金錢豹、黑鸛以及滇金絲猴的天敵金雕等。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全球環境基金會GEF、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以及大理大學東喜瑪拉雅生物多樣性研究院等諸多研究機構和公益組織,也先後加入到滇金絲猴研究與保護的大社區中來。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西南項目中心首席科學家、中國靈長類學會原會長龍勇誠介紹,由雲南大學、大理大學、阿拉善SEE和中國林科院組成的科研團隊,在當地護林員的協助下,開展了全境滇金絲猴種群、數量和分佈調查,初步估計滇金絲猴數量目前超過3500隻。
余建華的兒子十多年前已成為護林員。襁褓裡的小孫子還不滿周歲,老余也希望他長大後能將護林的事業傳承下去。◇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