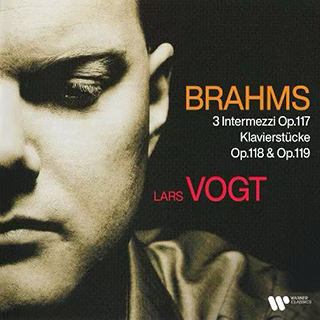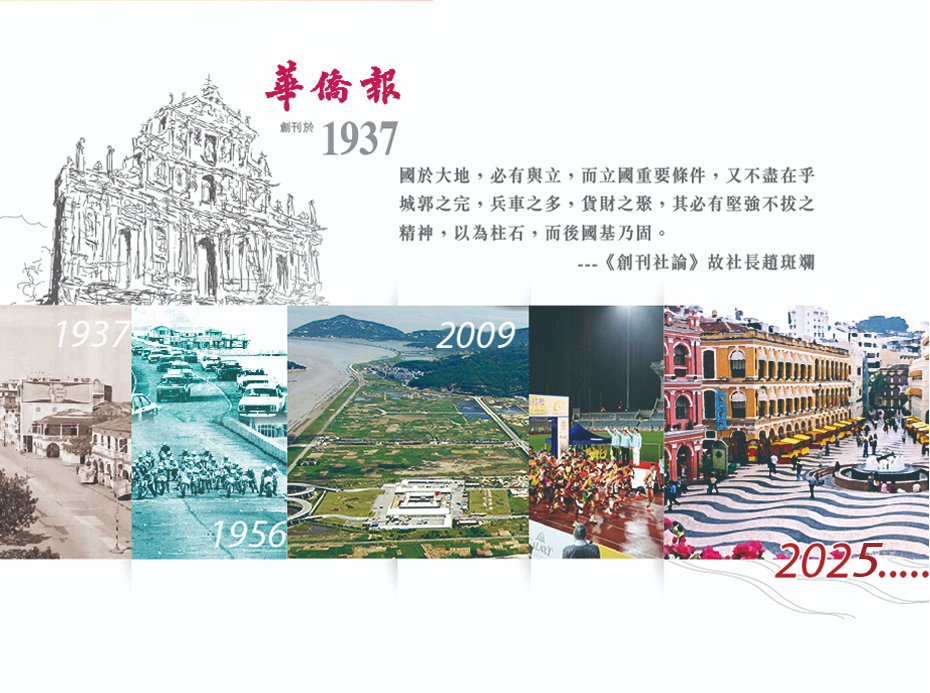關於連串布拉姆斯作品音樂會上座率低的問題,有人歸咎布拉姆斯音樂在本地的吸引力不如貝多芬、莫札特、柴可夫斯基、蕭邦等作品,這應是原因之一。
部份樂迷對布拉姆斯音樂可能較為慢熱,但只要相處一段時間,便慢慢察覺那默默流淌的內在美,一種沉鬱與深邃之美,含蓄與雋永之美,同時糅合著最激昂及最溫柔的情緒,映照出一份歷盡滄桑的怡然和豁達。相較於同期的李斯特或華格納,布拉姆斯毫不在意於情感的外露和張揚,他的音樂當然也有激情,但只向內爆發,不會在感官層面刺激你。凡屬精神層面感觸的事物,需經感官接收,再經咀嚼、消化,對應內心的美感經驗後,方能產生共鳴,這種感動固然是深層的,也許不那麼快構成情感激盪,卻從思緒中慢慢滲透,因而更深刻、雋永。在時間醞釀下,經過一些人生波折,你便會被那些苦澀中帶甘美的旋律打動。所以很多人都說,要步入中年才懂得欣賞布拉姆斯。
布拉姆斯創作態度嚴苛,顯然經過深思熟慮才發表作品,他的第一交響曲由構思至完成費時二十一年,作品出版時,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這種創作上的拖延,除因為嚴謹的處事手法,相信亦基於作曲家的自我懷疑。積極進取者會說這是一種性格缺憾,我們亦難以理解他為何如此「舉步維艱」,但反觀自己的生活,何嘗不是充斥著種種的「遲疑不決」和「有苦難言」?當我們步入中年,從前的願望隨風消逝,夢想逐一破滅,便更容易理解布拉姆斯音樂中那種「欲言又止」的美學,心領神會之後,對人生中碰到的「未竟之事」,便能釋懷,便能默然接受。他的第二交響曲的第二樂章和第四交響曲的首樂章,那種無奈——無為——無求的自我嘆息,映照的正是這樣的心境,所謂「要踏入中年才體會到的共鳴」,亦因此而起。
近年,筆者對布拉姆斯的晚年作品尤其感受深刻,我想起在剛過去的布拉姆斯系列音樂會中,俄羅斯鋼琴家沃洛丁(Alexei Volodin)彈畢《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後,為我們加奏了Intermezzi Op.117中的No.1,他以輕撫式的觸鍵呈現清澈透明的音樂肌理,傳遞婉約含蓄的美感,欲語還休的語調,反映一種風霜醞釀出的平靜心境。
布拉姆斯這系列作品包括Op.117(三曲)、Op.118(六曲)、Op.119(四曲),正是筆者近日在夜闌人靜時常聽的音樂。布拉姆斯晚年把最深刻、最親暱的情感埋藏這些小品式鋼琴曲中,交付發行前都先送克拉拉(Clara Schumann)過目,作品顯然蘊含他對克拉拉的深情。那種欲言又止的含蓄況味,在Op.117的No.1及Op.118的No.2中更被表達無遺,滄桑而帶點撫慰的琴音,儘管惆悵、戚然,但絕不讓你心碎,在淒清孤寂中,總透著一絲的溫柔與甜美。
很喜愛德國鋼琴家沃格特(Lars Vogt)演奏於二零零二年的版本,就Op.117的No.1而言,他的手法一如Alexei Volodin般理智,音色同樣透明,情感則沉澱得更為清洌。沃格特在演藝生涯剛步入輝煌時離開我們(二零二二年九月),在知命之年便與世長辭,實在令人扼腕痛惜,每次聽他這張布拉姆斯專輯,都教我惘然,慨嘆生命的無常。
最近結交了兩位醉心音樂的朋友,不足二十歲的年青人,卻鍾情於布拉姆斯的音樂,而且聽得較深入,欣賞心得說來亦頭頭是道,和他們談論布拉姆斯無疑十分投契,但知道他們的年齡後,畢竟有點意外。大概現代人的思想越來越早熟吧,「未到中年難以領略布拉姆斯音樂美」的局限,看來已被這兩位年輕人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