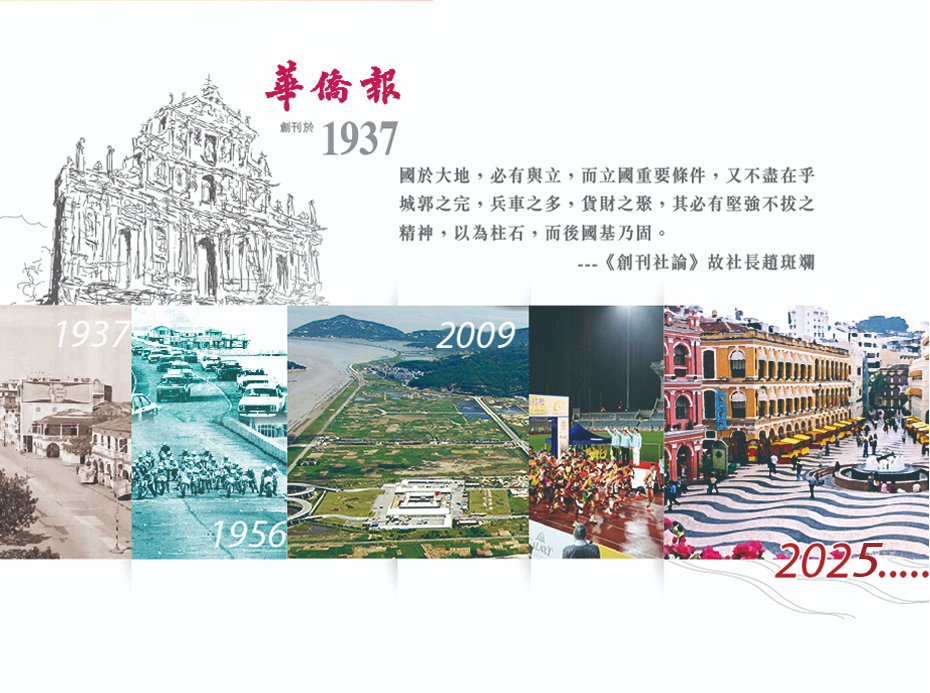你有完整地聽完一喝折子戲嗎?你還記得上次與朋友談到傳統戲曲是什麼時候嗎?你能念出三個中國戲曲界的代表人物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請來看看吧。
事情還要從一段對話講起。有一次,父親和我提起了他兒時過春節的事情,他說:「小時候,在鎮裡住,過春節時,最熱鬧的,莫過於看戲了。找一塊大大的空地,一個臨時的戲臺子,在上面鋪上紅布,再請一個戲班,吹吹打打、鑼鼓喧天,戲臺子下放上幾十排長椅,雷時村裡幾個機靈的少女每年負責上臺演花旦……「我已經聽得入了迷,想像看,火樹銀花不夜天,天上人間慶團圓。點翠行頭金龍袍,滿堂喝彩的畫面,那是獨屬於他們那個年代春節的喝彩,以至於根據每片土地的方言差異,同一臺戲在每了地方的臺詞與演譯手法也有所不同。甚至,人們閑下來還會通過本土流傳的一些故事,去編排出獨屬於這片土地的曲目。當年家裡的姑姑正讀高中,一次過年登臺演了花旦,看著我爸說至此處時不經意上揚的嘴角,我就知道,那年春節我們家一定過得很光彩。
那些戲班去哪了呢?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等了很久很久……
「你聽說了嗎?國家一團去珠海演出了。」老爸說,我當即從沙發上跳起來查詢資料,這可真把我激動壊了,國家一團,是中國國家戲劇團一團的簡稱。我們沒有絲毫猶豫,上網搶了幾個靠後的位置,本以為我是個誠意滿滿的觀賞者,沒想到,去了現場發現前面排隊的是幾個拖著行李箱的花甲老人,上前一問,才知道他們是北方人,國家一團在他們省舉行巡迴演出時,因為人太多了,所以沒搶到票,為了看到下一場,他們不遠千里來珠海看。我心裡一驚,一時間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他們的執著。或許這就是幾個老人對文化的致敬吧。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愛是不能用時問和空間量度的。這種愛,就如伯牙在桃葉渡送別子期後,伯牙丟下琴追上子期一般,但進入場館後,我才發現自己失算了,觀眾席裡好多頭髮花白的老人,有子女陪的、沒子女陪的,靜靜地坐著等開場。他們看著前方不知到什麼時候開場,我環顧左右也找不出幾個年輕面孔,這時,身後傳來了一個稚嫩的聲音,我小心地回頭看去,是一個小男孩,他身量小小的,坐在椅子上,腳還夠不著地;他旁邊是一位中年男子,正伏著身子,細細地和小男孩講著傳統戲曲的知識,從生旦淨丑,講到文武行當;從舞臺效果講到臉譜油彩。小男孩微微把頭側向父親,大眼睛直直地盯著臺上演員的一舉一動。此時,傳承在我眼前具象化了。
看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詞,民族復興。這就是我們國家民族復興上下推行的最好體現,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這是我們民族的底色,也是無數代先輩託付給當代青年的責任。◇